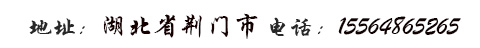游到汕尾,马鲛鱼就丸了
|
“ 跟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老婆饼里没老婆的情况相似,很多鱼丸里是没有鱼肉的,汕尾人吃到这种鱼丸可能会骂人。被假鱼丸「荼毒」多年的吃货,一旦吃到货真价实的汕尾鱼丸,恐是会分分钟领会到什么叫「日啖鱼丸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盒鲜姑 ” 某个工作日午憩,和同事开车到公司附近半山腰的大排档加餐。店家捧出一道香煎马鲛——鱼肉厚切,稍加盐渍,以猪油干煎,动物性油脂浸入肌理,洁白鱼肉外形成一层微焦的酥脆表皮,顿时成为众人席间心头好。 ▲香煎马鲛鱼的鱼皮十分酥脆 粤东有句谚语:「好鱼马鲛鲳,好菜芥蓝薳,好戏苏六娘」。马鲛鱼和鲳鱼,是乡人心目中并列最TOP的位置。马鲛鱼属洄游鱼类,银肤燕尾,味甜肥美,可惜自广东伏季休渔以来,市场上渔获渐少,新鲜的马鲛鱼也成为了食客们的意难平。夏秋求清淡,冬春偏浓醇,广东饮食虽素来讲究「不时不食」,但舌头和胃口终不会骗人,在马鲛渔汛之外的日子里,如何保留那一口鲜甜,便成为了老饕们一道永恒的课题。 ▲一条被冰藏的马鲛鱼 /分解和重构,封存那一口鲜甜/ 在笔者家乡广东汕尾,人们更愿意将新鲜的马鲛鱼制成鱼丸,当地人称之为「打丸」。 鱼肉在外力的作用下,被不断分解、组合、重构,纤维组织与盐分、水分充分混合,从而产生质的变化。有盐的加持,马鲛鱼丸在冰箱中冷冻数月,仍可保留极鲜的风味。 ▲马鲛鱼丸冷冻后也一样鲜美 汕尾街市上常见的马鲛鱼有两种。一种是「白腹乌绢」,鱼腹呈银灰色,体侧分布着蓝灰色圆形斑点,一直延伸到尾部,体态俊俏,滋味最美。 另一种是「竹筒」,体侧则是纵向纤细黑色斑纹,如同竹节,个头稍大,但味道却略逊一筹。 乡人「打丸」原料多为前者,母亲也不例外。「差一些就是差一些,嘴巴不会骗人」。 ▲许多市民会在渔港等待新鲜的鱼上岸 小时候,「打丸」是家里的一件大事。清晨,母亲早早就从街市拎回两条「白腹乌绢」,横置在案板上,焕发寒森森的银光,等候着进一步加工。 那时候,我常诧异于母亲为何对鱼身的构造如此熟稔,以致于我常怀疑她在偷看我的《自然》课本。 母亲提起菜刀,熟练地卸下鱼头和鱼鳍,再沿鱼骨剃下两片鱼肉,动作干净利落,不消一盏茶的时间,两条鱼便被分解妥当。 ▲熟练的人切鱼都很干净利落 为了成品的美观,母亲会仔细清除黏连在鱼肉上的血丝,甚至连鱼腹处稍显暗红的肉也会一一剔除,只留下两片晶莹剔透的白肉。 接着,用匙羹将鱼肉从鱼皮和鱼骨上细细刮下,同时抽出肌间细骨,一丝儿也容不得马虎。 鱼肉刮下后,便是剁茸。剁茸需要节奏,双刀飞舞,「哒哒啦哒……」声如马蹄轻疾。在刀刃下,鱼肉渐渐变成细茸,质地也愈发细腻、弹牙。直到鱼茸有些许粘刀,便可打浆。 ▲打出好鱼浆是要看好手艺的 在剁好的鱼茸中加入蛋清、盐水以及些许薯粉,再用阴力进行混合、揉搓、按压,同时打浆的节奏不宜过快,以免导致鱼浆过热,影响口感和风味。 过年回乡,听街市的鱼丸摊档说,现在也有直接用冰代水入浆,可直接用机器搅打,但至于风味,就另当别论了。 ▲鱼丸粉丝汤别提有多鲜了 /马鲛鱼浆,进退两相宜/ 搅打上劲的鱼浆,在乡人的丸子宇宙中,既是基底,也是主角。 进可兼济天下,配合猪肉糜、冬菇、虾米、鱿鱼,乃至铁脯粉(比目鱼干)等各色佐料,演绎出「肉丸」、「大粒参」等各种精彩,不停探索关于丸子更多的可能性。 退可独善其身,以纯马鲛鱼浆制丸,色白味鲜,封存了马鲛鱼所有秘密,乡人称之为「白丸」,在各色丸子中最受欢迎。 ▲牛肉在广东也逃不过做成丸子的命运 一旦鱼浆备好,「白丸」的制作和烹饪都极简单。 鱼浆从手掌的虎口处挤出,再用匙羹沾水舀下,形成一个圆滚滚,白丸子。而后,将丸子依次排列在铜盘上,再大火蒸十分钟即可。 母亲每每在蒸丸子时,总得自己配音。仿佛没有声音的加持,丸子会在揭盖的一刻泄了气,白白少了几分美味。 揭开锅盖的一刻常常是「哇」的一声,尾音悠长,一边念叨着「今年的丸水」,水为乡音,即漂亮的意思。而我早早就守在灶边,没等母亲话音落下,便狼吞虎咽起来。▲新鲜出炉的马鲛鱼丸是最好吃的 /才下胃口,却上心头/ 鱼丸在我家除夕围炉中,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菜,寓意着团圆美满。今年疫情期间,小叔整理出年家里除夕围炉的录像,发至家里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weizx.com/swbk/17883.html
- 上一篇文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调研指导汕尾惠州脱贫攻
- 下一篇文章: 气象百科气象学上的神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