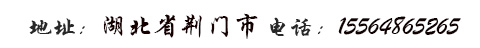巴黎烧了吗
|
治疗白癜风医院哪家好 http://pf.39.net/bdfyy/
瓦叔评论: 我们当初在刚刚入行的时候,经常会讨论一些经典的入行必读书目。在这些书里,一目了然,比如《故事》《普利策奖特稿卷》,有些书有点可怕,比如《冷血》《刽子手之歌》,有些很有诗意,比如《大地孤独闪光》。但我清晰地记得,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书名只有一本,叫做《巴黎烧了吗?》。几乎是看到这个书名就让我产生了阅读欲望:为什么要将问句做为书名?难道巴黎烧没有烧,还会有疑问吗?而且为什么巴黎会烧起来?什么时候烧的?谁在烧? 这种好奇使我当时就买下了它,然后欲罢不能。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让人充满遐想的标题,也许正是这两位讲故事的大师抛出的第一个鱼饵,当你对它产生了兴趣之后,你就会发现,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在等着你。这本书,就像我下面给大家展示的段落一样,正是由无数这样紧密连接的一个一个的悬念、人物、细节、事件组成的。而这些事件、细节,又随着事物发展而彼此交叉,像无数的经纬纵横,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年,盟军登陆法国,即将解放巴黎,然而第三帝国的军队仍然盘踞法国,希特勒更是叫嚣要给法国人留下一片废墟。武力解放不仅旷日持久,牺牲巨大,而且意味着巴黎必将生灵涂炭,千百年来的法国荣耀将付之一炬。围绕法国如何解放,盟军、德军、目标一致却又貌合神离的法国抵抗军、以及巴黎的普通平民在八个月里开始了复杂的博弈。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法国版本的《北平无战事》。准确的说,它要复杂的多得多: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恰恰不是用某一两个人的故事构成主体,而是涵盖了当时多方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们的视角,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细节。当你要用如此之多的人的故事来汇聚成一条整体的故事线的时候,困难是可以预见的:你怎么让人不会感觉自己在看一堆随笔呢?你如何协调不同地点、不同事件、不同“画风”?你怎么把它们的故事恰如其分的构成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的紧密结构,以至于最后能够形成一本完整的厚书? 答案是可以想见的:扎实的采访,对细节的深究,还有长期的写作功力,让我们来记着两位作者的名字:美国记者拉莱?科林斯以及法国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为了写成此书,他们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书里每一个细节看似是“戏剧”,实际上都经过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多次核查。难怪读库的张立宪老师如此评价:“许多人宁愿轻轻一笔带过,却并不愿意下笨工夫去寻幽探微,事实上,结局并不值钱,道理也不值钱,过程中的细节才值钱。” 巴黎烧了吗 作者: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翻译:董乐山 1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每天傍晚,那个德国兵带着他的那支旧毛瑟枪、皮套已经磨得发毛的望远镜和装了晚饭的饭盒一到,梅昂默尔田村子里的居民就知道已是六点钟了。他走过村里的鹅卵石铺的广场时,12世纪盖的那座小小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就分毫不差地开始响起晚祷的钟声。那座小教堂高踞在巴黎东北37英里处乌尔克河畔的一个小山脊上,俯瞰着梅昂默尔田村的灰瓦屋顶。 这个德国兵是个头发花白的德国空军中士,他总是迎着清脆的钟声走来。他在教堂门前摘下军便帽后走了进去。他用缓慢的步子爬上狭窄的螺旋形楼梯,到了钟楼顶上。那里有一张桌子,一只煤气炉,一张从下面教堂那里征用来的椅子。桌子上整齐地铺着一张德军总参谋部军用地图,还有一本笔记簿,一本日历,一台灰绿色军用电话。圣母升天教堂的钟楼是德国空军的一个望哨。 那个德国兵在这里用望远镜可以把这一带整个地区都收入眼底。从南面莫城的大教堂尖顶到北面拉费尔特米隆堡的中世纪石墙,他极目望去,纵横13英里,眼光扫过了马恩河弯弯的河道,乌尔克河畔利赛镇的陶砖墙头,最后回到了在他眼皮底下蜿蜒而去的乌尔克河白杨参天的河岸。 再过几小时,夜幕就会降落在这位中士的望远镜下一览无余的宁静景色上。那时他就要搜索天际,窥看周围的黑影,又一次开始他的夜间值勤,这已是诺曼底登陆以来的第58次了。等到东方发白,他就会提起军用电话,向设在苏瓦松的德国空军分部报告。自从12天前上次月圆以来,中士的报告总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句话本区没有情况。” 这个德国兵知道,盟军总是在满月时的月明之夜向法国抵抗运动作降落伞空投的。他桌子上的日历告诉他,要再过16个夜晚,到8月18日晚上,月亮才会再圆。 这个德国兵心中很有把握,那天晚上,在交托给他看守的法国占领区这块小小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此在年8月2日这天晚上,这个中士觉得他完全可以趴在他面前摇晃不稳的桌子上放心地打个盹。可是这个德国兵错了。 2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两英里外一片堆着一捆捆麦稻的潮湿的田野里,有两男一女散了开来,布成了三角形的阵势,那是抵抗运动空投区的标志。他们的手中都握着手电筒,玻璃罩外面装了用马口铁皮打的套子。这种装了套子的手电筒发出的是一道细细的光柱,只有从天空中朝下看望才能看到。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午夜刚过不久,他们就听到了他们在等待的声音。那是一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把发动机降低马力后轻轻地飞过乌尔克河谷时发出的低低的嗡嗡声。他们打开了手电筒。 上面那架飞机的驾驶员低着头看望下面灯火管制下的漆黑河谷,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手电筒的三角形闪光。他按了一下面前的控制盘上的一个按钮。飞机机舱里有一盏灯由红变绿。这时有一个人扶住飞机上打开的舱门,纵身一跃,跳入夜色之中。 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子后跟里嵌着一块薄如轻纱的绸子。上面印有十八列密码数字。他在伦敦的上级认为上面的信息十分重要,十分火急,因此不惜违反他们的一切规定,派阿兰?佩帕扎冒险在这无月的黑夜跳伞投递。 佩帕扎并不知道他投递的是什么信息。他只知道要尽快把它送到潜伏在法国的英国谍报机构一个代号叫“阿米可翡翠”的头子那里。他的总部设在巴黎。 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九个修女跪在她们的教堂的清凉的阴影里,正在诵念她们这一天诵念第三遍的祈祷文,这时有三长一短的门铃声刺破了修道院的寂静。她们之中有两个修女马上站了起来,划了为自己祝福的十字,走了开去。对院长妹妹简恩修女和她的助手简恩玛丽?维阿内修女来说,拉圣特路号修道院古老的门铃三长一短的铃声意味着“有要客来访”。 德国秘密警察四年来一直在竭力搜寻藏匿在这个修道院里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在院内一块空地和圣安妮疯人院尚尚的石墙交接处,有一所表面粗糙不平的旧房子,在这房子的起居室后面,就是法国占领区英国谍报头子“阿米可翡翠”的总部。在这些古老的石墙和几个修女的镇定自若的勇气的保护下,他的总部一次又一次逃过了德国秘密警察的严密搜查。 3 对“阿米可翡翠”修道院围墙外面这个城市来说,这个炎热的八月上午是德军占领的第天。 十二点钟刚刚敲响,二等兵弗里茨?戈特却尔克就像他在过去四年中每天做的一样,和他的第一保安团的名弟兄一起,开始他们每天沿香榭丽舍大道开到协和广场去的列队行进。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支铜管乐队吹奏起“普鲁士光荣”的剌耳音调。很少有巴黎人站在这条气象宏伟的大街的人行道上观赏二等兵戈特却尔克的表演。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躲开这种令人羞辱的场面。 这种趾高气扬的列队行进不过是法国首都从年6月15日以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许多羞辱之一而已。那一天法国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国旗在巴黎公开陈列的惟一地方是在空气污浊发霉的荣军院博物馆里,而且还是锁在玻璃柜里的。 纳粹德国的黑白红田字旗则在巴黎市的象征——埃菲尔铁塔顶上飘扬。被巴黎的征服者所征用的成百上千所旅馆、公共建筑、公寓大楼的顶上,都飘扬着这面令人感到压抑的旗帜,那是四年来钳制着世界上这座最美丽的城市的精神的那个政权的象征。 沿着里沃利路上优雅的拱廊,在协和广场四周,在卢森堡宫、国民议会、外交部的前面,德国武装部队的漆成黑白红三色的岗哨挡住了巴黎人,不让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的人行道上行走。 在福煦大道74号和索色埃街9号门前,在其他一些标志不这么明显但同样著名的建筑物门前,站岗的是德国武装部队之外的部队。他们的军服领口上有党卫军的双条银色闪电。他们守卫着秘密警察的办公楼。他们的邻居晚上总是睡不好。因为从这些建筑物里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传出惨叫声来,要听而不闻,常常是很难做到的。 德国人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把全市近二百座最漂亮的铜像都拆卸了下来,运到德国去熔化,制造炮弹的弹壳。 工兵劳役队里的建筑师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来取代这些铜像,也许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要差一些,但是却要威风得多。几乎有一百多个混凝土地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的人行道上。它们的矮墩墩的形状分布在全市各处的地面上,仿佛是青春痘一般。 巴黎的宽阔的林阴道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荡过。没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早在年就绝迹了。少数运气好的(或者说没有骨气的)司机弄到一张德国牌照,把汽车改装,在车身后面绑上一个小锅炉,用木柴当燃料来发动。 不过,据伊里奥特?保尔的回忆,巴黎还是保持了它的“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骑车的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七月间,时装设计家玛黛琳?德劳什、吕西安?莱朗和杰克?法恩发布了“军人式”的流行款式。它的特点是肩膀宽、腰带宽、裙子短——这是为了节约用料。法国衣料短缺。有些料子是用木头纤维做的。巴黎人开玩笑说,这种衣料淋了雨,白蚂蚁就都爬出来了。 晚上,巴黎人穿着木跟皮鞋在街上走,格格声不断。他们学会了万一过了宵禁时间就脱了鞋子,光着脚回家。那样巡逻的德国兵就只听见自己的皮靴铁掌击地声了。 那年八月,巴黎人都呆在家中。战争使得大家都无法按惯常那样到乡间去度假。学校照常开学。成千上万的人在塞纳河的河滨道上晒日光浴。那年夏天,这条泥浆污浊的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随便哪个巴黎人那天晚上往窗外看,就可以看到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巴黎仍完好无损。圣母院、卢浮宫、圣心教堂、凯旋门,所有这些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物曾经使这个城市成为文明人类的灯塔,而在这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五年来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如今,巴黎的解放时刻终于快要来到了。在这八月的晚上把华沙化为一片瓦砾的命运,也就是巴黎到现在为止像奇迹一样逃脱的命运,很快就将笼罩在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的头上。 4 这时有一个忧郁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炎热的夏季气候中不耐烦地等待着。对他来说,巴黎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不久将随之而转的关键,也是这个孤独的人自己的命运随之而转的关键。因为夏尔?戴高乐比他周围的人更加明白,他于年6月18日从伦敦向他的战败的国人发出的那个号召是一场大胆的赌博,而巴黎是决定这场赌博输赢的地方。戴高乐深信,在今后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决定由谁来控制战后法国。戴高乐将军坚定地决心要由他来控制。 戴高乐相信,有两派的人阴谋不让他得到控制权:一派是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法国共产党,另一派是他的军事上的盟友美国人。 美戴关系在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承认维希政府、同达尔朗的交易、美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才告知戴高乐、戴高乐同罗斯福之间的个人厌嫌——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法美之间互不信任和猜疑,影响年夏季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有比罗斯福拒绝承认他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更加激怒戴高乐了。他认为这是美国拒绝承认他对法国的领导地位。 巴黎城内如果发生起义将会是一场灾难。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也发出了坚定的命令防止这样的事发生。 4 在巴黎郊区奥特伊一幢五层楼公寓的顶楼上,接到戴高乐这个命令的人,呆呆地站在窗口,凝视着窗外八月的黑夜。在灯火管制下,他只能依稀看出在他前面连绵不断延伸到远处天边的高低不齐的黑影,那就是巴黎的屋顶。这个人名叫雅克?沙邦戴尔马,年仅29岁,已是一位将军了。那天他另外又接到一个信息,那是在街角修理自行车车胎的人悄声告诉他的,也就是“阿米可翡翠”几个小时前在我主受难修道院译出来的那个信息。 在阿兰?佩帕扎左脚鞋跟中带来的情报,对巴黎的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没有像对这个沉思的年轻人更加具有灾难性了。 沙邦知道,在戴高乐将军的眼里,他所交给他的任务中,没有比派他在巴黎的任务更加重要了。在他从伦敦戴高乐军事总部收到的秘密指示中,也没有比他收到的关于巴黎的指示更加清楚和明确了。 他要对巴黎市内武装的抵抗运动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让首都发生未经将军直接授权的起义。 这个命令是不可能办到的命令。 沙邦并不控制巴黎的抵抗运动。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共产党。 他相信,“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遭到毁灭。”沙邦意识到,“巴黎是共产党决不会白白放过的一个机会。” 他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放过这一机会。但是他一无进展。沙邦的共产党对手是个生活俭朴的建筑师,名叫罗杰?维戎,他认为戴高乐派所以要防止起义,是因为这样“戴高乐就可以率领一支征服大军开进巴黎。看到整个城市感在巴黎攫夺政权。然后把戴高乐当做他们邀请的客人而不是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来欢迎。” 像巴黎的其他人一样,沙邦在那天晚上也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而几个星期以来,要使巴黎免遭这个厄运,他心里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盟军解决了诺曼底以后就会直捣巴黎,抢在共产党组织暴动之前占领巴黎。但是阿兰?佩帕扎左脚鞋跟带来的信息打破了这个希望。在熄了灯火的寂寞的公寓中,这位年轻的将军现在觉得,盟军的计划正好直接把球拱送给他的共产党对手。 沙邦相信,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等待着巴黎。 或者是报复心切的德国国防军粉碎了起义,并且随之粉碎了巴黎,或者是起义胜利的共产党领袖在首都的权力堡垒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准备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整个法国。 那天晚上,在沙邦看来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难题。他必须说服盟军改变计划。他必须把巴黎的情况报告给戴高乐。看来他必须做一次像阿兰?佩帕扎那样的旅行,只是方向相反。他要设法到伦敦去。他在绝望之下,鼓起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气,决心要向艾森豪威尔恳切陈词,力求他改变计划,把装甲部队直开巴黎。 5 但是那个躲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钢筋混凝土地堡中指挥第三帝国各路大军的德国人,却有他自己的扭曲的推理方式,根据这种推理,巴黎也许还有更多的意义。 像戴高乐一样,希特勒知道,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曾两次进攻巴黎。不久,历史的捉弄将使他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次,希特勒将成为巴黎的守卫者。盟军总部的计划人员知道,希特勒有一切理由拼命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为他提供的“天然屏障”。丢了它,他也就要丢掉他的火箭发射场,眼看盟国大军兵临帝国大门。 希特勒不久就会决定他怎么保卫巴黎,就像他决定怎么保卫斯大林格勒、卡西诺山和圣洛—样。在几天之内,在东普鲁士这个地堡里,他将命令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用拳头猛击橡木会议桌,对他的心存疑虑的总参谋部人员尖声嘶叫: “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 6 饱经战斗而疲惫不堪的德国国防军士兵站满了与铁轨平行的混凝土站台上,他们的年轻的脸像一个个神情冷漠、听天由命的面具。他们马上就要爬上停在他们前面的“前线休假列车”,在火车头喷出的一阵蒸汽中,缓缓开出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东部前线去。 一个身材矮壮的国防军少将慢慢地从站台上的人缝中走过来,他以同情的眼光瞄了一眼他们的没有表情的脸。他也常常站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车站上,在一片沉默无声中,等待这同一列车把他带回到前线的战火中去。但是今天晚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搭的是另外一列火车。他的勤务兵提着衣箱跟在他的后面,肖尔铁茨走过站台上最后一排士兵,向那列火车走去。在这列蓝色卧车车厢的上面,肖尔铁茨还可以依稀地看出褪了色的黄色法文字母,令人想起了欧洲和平时期的火车旅行。但是在今天晚上,国际卧车即欧洲快车公司的这些车厢属于“总参谋部元首专车二列”,它将要把肖尔铁茨和一批显要的客人送到东普鲁士腊斯顿堡希特勒的大本营去。 肖尔铁茨登上了为他预定的车厢,开始解开军服的纽扣。他看着勤务兵小心地把他战前买的吉列剃须刀、肥皂和一瓶安眠药放在洗脸盆的擦得锃亮的红木盆架上。他知道,等会儿他得要感谢这些安眠药为他带来睡眠。明天早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受到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的亲自接见。 年那个夏天,很少有陆军元帅被召去见希特勒。他肯不吝时间接见的将军就更少了。肖尔铁茨被召去有一个特殊原因。躺到卧车车厢棕色丝绒卧铺上去的这个矮壮的普鲁士将军是阿道夫?希特勒选来负责指挥法国首都的防务的。 三天前,在这列元首专车载着他去的那个大本营中,有个人从保险室的档案铁柜中选出了三个将领的档案。其中一个就是肖尔铁茨的档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将军马上被肖尔铁茨的档案所吸引了。尤其是,它表明肖尔铁茨是一个对第三帝国始终忠诚不渝的人。伯格多夫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巴黎。失败和不忠的情绪已经在将领阶层蔓延开来,中毒之深莫过于巴黎。驻法资深将领卡尔?海因里希?冯?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是7月20日图谋杀害希特勒的头目。失败以后,他自杀未遂,眼睛已瞎,那天晚上仍半死半活地躺在柏林普洛成湖监狱的床板上。过不了很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他就要被绞死。喜欢附庸风雅的大巴黎司令汉斯?冯?波因伯格朗斯费尔德将军,在伯格多夫看来,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伯格多夫知道,在巴黎今后困难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需要一个其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恢复该市纪律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伯格多夫知道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 在他看来,肖尔铁茨似乎就是这个人。伯格多夫把他的档案拿去,亲自放在元首的面前。他推荐说,肖尔铁茨就是他们该派去巴黎的人选;他是“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而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元首表示了首肯。但是,他继而一想,又加上了一个特殊要求。他觉得巴黎的任命极其重要,因此叫伯格多夫把肖尔铁茨从他在诺曼底的兵团司令部召到最高统帅部来,亲自任命。 7 对于这个因其忠诚无懈可击而被希特勒决定派往巴黎的军官来说,战争是年5月10日5点30分开始的。冯?肖尔铁茨中校那天早晨率领空降步兵第一六团第三营从第一架JU52飞机中跳了出来,空降到鹿特丹机场,第一个在西线实现了德国的闪电战。他是攻进荷兰的第一个德国军官。他的任务是占据该市南面不远的新马斯河上的桥梁。经过四昼夜的激战,荷兰人继续抵抗。到5月14日中午,肖尔铁茨命令一位牧师和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荷军指挥员投降。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不投降,“鹿特丹将遭无情炮轰。”两小时后,他们没有找到荷军指挥员就回来了,于是攻击开始。肖尔铁茨等到攻击持续了足够长久以后,就想发个信号弹停止攻击。但他后来说,信号给附近起火焚烧的一辆货轮的烟掩遮了,炮轰继续不断直到最后。据荷方估计,死人,伤人,包括无家可归者。炮轰毁掉了鹿特丹的市中心。 后来有个朋友问他,他率领军队进攻一个德国对它没有宣战的国家有没有感到良心不安。 “为什么?”他回答。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从小所受的教育可不是教他来问“为什么”的。他生在他家在西里西亚世传的树木茂盛的庄园中,从他哇哇落地之时开始,他的命运就已决定了。在他之前,有三代普鲁士军人从这庄园的灰瓦高塔中产生。他是在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受教育的。由于他的表现突出,他被选去在萨克森王后的宫廷中当侍童。 冯?肖尔铁茨一生最自豪的时刻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擢升为将军的。这个黑海港口围城开始时,他的团共有官兵人。到年7月27日,只剩下了人。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尽管右臂受伤流血,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毫不犹疑地强迫俄国战俘为他的攻城大炮搬运炮弹和装炮弹。说实在的,他觉得强迫俄国人为他的大炮装上去炸毁他们的家园的炮弹很好玩。 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集团军,肖尔铁茨运气不好,奉命率师掩护一支后撤的军队的路线。像往常一样,他忠实地执行了他接到的命令。在年这些艰苦的日子里,他接到的命令是在后撤的国防军身后要做到寸草不留,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毁坏。 这位等待着元首专列把他送离西里西亚车站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将军却要带着毁灭城市专家的名气去巴黎。这个名气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日后他会在巴黎向一位瑞典外交家承认,“自从塞瓦斯托波尔以后我的命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更多考研资讯 可移步瓦叔的新浪微博 SinaWeibo:传播学考研就找瓦洛佳 perasperaadastra尽吾之力以达天际 我们致力于让你在新传考研路上Makeyourdreams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weizx.com/swys/20836.html
- 上一篇文章: 自然要素河湖综合题20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